对“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回望与思考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号
作者:赵园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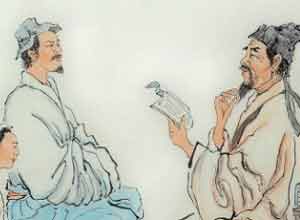
《家人父子》是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而且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收官之作,今后可能做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了;会用学术方式,会遵守学术规范,但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说“收官”我怕有点自我炒作的味道,有人想到收官就会有好奇心,我看她怎么收官的,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事实,就是到此为止。我画条线到此为止,今后不再做了,还有题目,还有材料,但是不做了。我觉得那些题目别人做很可能做得更好。
我在台湾跟明史界的同行说——面对同行大家就不必客气了——我说这本书叫《家人父子》,大概有点勉强,因为它可能有7/10的篇幅是关于“夫妇”的,关于“父子”大概只占3/10,大家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个更好的书名?但是直到我交书稿的时候,仍然没有人在这方面帮我一把,所以就索性叫《家人父子》了,因为这个题目稍微宽一些,和内容也还算一致,所以就用了这个题目。
我在北大跟同学们讲《家人父子》的时候说过,我在伦理问题上有一点特殊的敏感,有时候甚至有一点自虐的倾向。我常常会很久之后还记得,甚至几十年前看到的都会记得很清楚,这好像像是虐心的那种行为,自己完全不能克制。比如现代文学,有两篇小说涉及母子的,我都很难忘记。一篇是蹇先艾的《水葬》,他写一个贫苦农民偷了点东西,大概是小偷小摸之类,当地乡民为了惩罚他,把他沉船了,水葬了。可是那天晚上,他的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还在家门口的场院上等着他归来。这个小说就使我无法忘却,我会反复地想,这个老母亲等来的会是什么?下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篇是蒋光慈的《田野的风》,可能搞现代文学研究的是知道的。一个革命者他在当地发动农民,搞农民运动,农民要去烧他自家的庄院,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很矛盾,矛盾在什么地方呢?他想到了他卧病在床的母亲。我想就是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当时革命和恋爱的关系,曾经被热炒,其实我也并不认为那就是伪命题;但是最终大家都能够了解,革命和恋爱是可以兼容的。
然而还有一个难题,比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关系更难处理,就是革命和家庭、亲情。我现在也不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应该如何,应该怎么样,就像古人说的忠孝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之处。有时候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你确实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是这,或者是那,不可能兼得。我就想,这个革命者该怎么做呢?我为他想不出一个解决问题之道。革命和家庭、亲情,现在是不是有了讨论的空间呢?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这仍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媒体上报道,有的革命者,在自己的晚年,他想起当年出走之后,他从成都出走,事后才知道,他母亲哭瞎了眼睛。然后他说他1964年回到家乡,他到晚年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向他母亲下跪。我看了这个回忆就想,你1934年离开家,为什么到1964年才回去看你的母亲,你1949年就可以回去。我觉得这些故事该怎么解读呢?这个跟我们这个题目不能说毫无关系,事实上写到最后,在我背后推动我做下去的一个推动力,是对于当代伦理问题的关心。我认为我们的文宣应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这样才有利于重建我们关于家庭的价值观。
二
我们接着还是讲当代的问题。上次在北大谈到,我在这本书的余论部分,涉及当代农村的伦理状况。过后一个小朋友跟我说,你说的状况并不是近些年才发生的,我想他应该指的是在现代史上,农民离乡到城市谋生就已经发生了,当然你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事实上传统社会,自始至终内部都有解构它的倾向。但是我仍然要说,像这种巨大的、剧烈的、结构性的变动,仍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才发生的,尤其是城市化、城镇化,大批农民进城。这个小朋友说的那种情况,可能在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小说中写到的很多都是限于东南沿海地区,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北方这种情况很少,对农村也没有造成结构性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最近我读到贾平凹的一篇文章,说美丽乡村这些很好,关键问题是乡村没有人了;其实也不是没有人了,有的是老弱妇孺,没有能力到城市谋生的人。因为他是陕西人,是商洛这一带的人,他说一条沟一条沟的村庄消失了。这种情况绝不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的,虽然梁漱溟也说过乡村结构性变动,其实发生得很早,甚至不只是始于近代。这些问题都应当说是我写这本小书的背景的一部分,因为我要不断往返于明清之际和当代。待会儿我还要说到,写这本书有些地方,有些章节,有些题目,事实上是很有痛感的。并不是做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有痛感,但是我做这个确实有痛点、有痛感,有感同身受的那种痛。
再谈谈古代和当代的有些不同,即使中国古代私域和公域的界限不是很分明,但是我写《家人父子》的时候,还是注意到了,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他区分得很清楚。比如我写祁彪佳,据说他一表人才,夫人又很美貌,在当时被人称为“金童玉女”。但是他是一个很强悍的官吏,诛杀起来毫不手软,而且确实有能力。但是回到家里,扮演家庭角色的时候,是一个很温存的丈夫。最后自己自沉殉明,甚至没有拉着老婆跟他一起死。那时候拉着老婆,拉着妻妾,拉着一家人同死的大有人在,但是他这时候仍然保持了他对家庭的那种温情。他把臣子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分得很清楚。
人伦之变,不仅特殊时代有,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就是和平时期、平常岁月都可能发生。比如我写到刘宗周门下一个知名的儒者张履祥,他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他的女儿被他的女婿和妾毒杀了,周围的朋友都劝他不要深究。张履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自然是很痛苦的,这就叫做人伦之变。但是这种人伦之变还不只是发生在张履祥一家,这种事情并不是非要到明清之际发生易代才有,但是一旦发生在明清之际这样的瞬间,人们马上会把它嵌在当时社会的大图画中,好像所有家庭事件、社会事件都必由当时的大背景来解释,这可能也有误区。其实在这样的时刻有变有常是很正常的,在动荡的时世,比较稳定的还是家庭、家族、宗族等等。有可能是个安全港,有可能是个避风港,但也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家庭你何尝可以小看它呢?它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总之它很重要。
三
我刚才说了,写这个过程中,确实是有痛点、有痛感的,但是我也注意到,不要滥情。我是研究文学的,但是我做学术和写随笔,我是把它们严格区分开的:个人情怀有时候我会用随笔的方式表达,前后有三四个随笔集,那里面都有表述我的个人情怀;但是做学术我还是很节制,而且严守学术规范。
比如我也用随笔的方式做过明清之际的有些题目,写过一篇比较长、一万多字的文章,是讲清初庄氏史狱中的几个人物,那就是用随笔写的,跟做学术是用不同的方式。关于清初的文字狱,杨念群先生比我熟悉得多。我为什么用随笔写,而不做学术论文呢,因为我没有把握把它做成学术论文,我没有充分研究别人在这个上面做了什么,哪些是别人没有说到、没有想到而我说到、想到的,在没有想到之前我宁可把它写成随笔,而不是做学术论文。
我后来看到两篇关于《家人父子》的随笔类的文章,是讲读后感的,有一点出乎我意料,这两篇文章几乎都对冒辟疆表达了义愤:这真是一个渣男,他配不上董小宛这个女神!(笑)会有这样的反响,我觉得很奇怪,我绝没有不能容忍冒辟疆的意思。反而我觉得冒辟疆这么坦然、这么坦白地讲自己的家事,不只是跟董小宛,包括和他的妻子,包括和他的弟弟,有的会被认为是丑闻的,他都白纸黑字写下来。当然了,那个文集是他的后人整理的,我不知道冒辟疆愿意不愿意把有些东西收入文集,反正是收入文集了,我看到了,后人看到了,这些材料很宝贵。而且冒辟疆做的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
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知名的人物,就是吴梅村,他有一个比较相好的风尘女子卞赛,也是向他表达了这个意思,要跟他,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想找一个归宿。但是吴梅村装聋作哑,不反应,然后卞赛就放弃了,当然她内心很痛苦。过后吴梅村在一个小诗中写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什么反应,过后怎么样与卞赛重逢,重逢之后的情景。我在这个小书的附录谈到,吴梅村毕竟是个大家,就笔力而言他是胜过冒辟疆的,他写得更有力量。吴梅村并没有表示悔意,因为他不能接受卞赛有各种原因,尤其是家庭的。他要想到为一个女子负责,他不答应也可能是一个负责的态度,所以大家不要对冒辟疆过分苛责,我们不能够这样苛责古人。我们只能够苛刻一点要求我们自己,但是不能够要求古人像我们一样。我看到这样两篇文章,觉得有点出乎我意料。而且我觉得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婚姻生活,应当有更丰富的了解。我希望这本小书,能丰富大家对于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理解。
四
我的学术背景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在今年是个热门话题,现在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讨论会。我在各种场合都说,我现在的认知,不足以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基本的判断,包括家庭压抑性,包括家族,男女不平等,女性受到的压迫等等。但是,至少这本小书会丰富你的了解,并不到处都在压迫,到处充满了苦难。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时有一首歌,“旧社会一口苦井万丈深……妇女就在最底层”,到现在我还记得这首歌。当然这里有一些基础判断,并不应当颠覆,但是确实,无论士大夫还是普通人,他的生活中,婚姻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家庭内部的生活,都是各种各样的。不妨展开你想象的空间,敞开一点,能够想象别种图画。比如这里引用了一种说法叫“古风妻似友”,这是归庄说的,归庄显然跟他的夫人关系很好,他的夫人从诗里看,是一个精灵古怪、极其聪明的女子,归庄和他的妻子的关系我是相信的。
但是我也注意到,我没有看到有人说“父子似友”的,父子似友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未必没有,但是我至少没有看到过这种表述。别人来提醒我,说汪曾祺有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个很有名。昨天晚上我和一个老同学一起用餐,我还问他“多年父子成兄弟”有所本吗,古人有类似的说法吗,他说好像没有。汪曾祺这么一说就成了名言了,但是古人未必没有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种现象,只不过没有这种表述。但是父子关系,在我的感觉中,确实更有压抑性。所以我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就自我解嘲吧,也是归之于父子关系本身的问题。但我也想过是不是我找材料的方向有问题,是不是有材料,在某个地方,而我没有注意到,我的视野有问题。所以这写得最薄弱的部分,我希望在座有人重写,或者把它做一些重大的增补。
这本小书更接近于文学,因为材料大部分是传记材料。当然我关于明清之际研究的材料是因为所做的题目而逐渐扩展的。比如做《想象与叙述》,我才读南明史的著作,或者开国史我都是这个时期读的,并不是一开始做明清之际的题目就先来读别人写的史学著作的。传记材料也是,因为写到《家人父子》,你只能在传记材料中寻找线索,这时候我才回头来看传记线索。原来我看刘宗周,主要看他作为忠臣的一面,他是一个名臣,而且是一个大忠臣;这时候我看刘宗周注意力就集中在他写他和他夫人的关系,以及他儿子写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动人。而且我注意到这一点之后,我对刘宗周有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原来在我的想象中,刘宗周也像别人写的那样,面目严冷,确实是一个道学之人,而且是一个“粹儒”,那是毫不含糊的,但是看到这一点,他怎么对待他的亲人,很动人。那些大名士不一定都可以做到,而且那些大名士有的在迂腐程度上还超过了刘宗周。我觉得刘宗周特别真诚。
我要承认我很难进入理学脉络,所以对于刘宗周理学那一面确实了解得不能说深入,但是我相信他很真诚。另外他扮演家庭角色的这一面,不只是他成了一个“粹儒”之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的人性中就有温情的一面,面目严冷是别人的感觉,也有人说到了晚年在他面前也是如坐春风。
这些传记材料并不是都可靠,因为“谀墓”即奉承死人也是一种传统,现在大概这个传统仍在,大家会恭维死人,而且觉得有些文字里不便说人家的坏话,揭人家的短,所以墓志铭、传这些都不可全信。因为我不是做传记研究的,所以没有愿望做考据工作,我觉得他写的即使是有作伪的成分,也能够表明他所认为的理想的夫妻、父子或者理想的人是什么样。所以这些传记材料,最好搜罗的范围广泛,并存异说。古代有一种治史、写史的方式是纂辑,它并存异说,不做判断,“传闻异辞”,可以打开想象的空间,未尝不可。现在正史一般不会用这种写法,但是我想个人史学的著作,仍然不妨采用这种写法,这样也可以使你有更大的选材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