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性还是改造人性?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羽戈
如今一说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及其改造,我们首先会想起鲁迅先生。事实上,国民性属于舶来词,从欧洲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到中国(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395页),并非鲁迅独创;而且,国民性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亦非鲁迅首倡,早在他之前,严复、梁启超、辜鸿铭等人都曾就国民性问题大发宏论,甚至还有更早的先驱,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撰《中国人的气质》,“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屡次推荐这本书,认为“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虽然错误亦多”,“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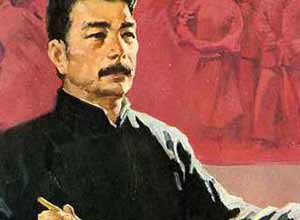
我们谈国民性,必须注意这两个细节。先说第一个。舶来的词语、理论,常常遭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转译困境,譬如封建、左右之争,其中国形象与西方形象如同驴头与马嘴,相去甚远,几乎完全错位。国民性的错位程度,相比封建,不算严重,这个橘子,移植到中国,依旧是橘子,不过却注了水,以至破坏了内在脉络。质言之,在西方,国民性有其正当性,国民性理论有其用武之地,可在中国未必如此。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所谓国民性,顾名思义,指一国人民的共同性格,那么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必定会具备一些共同性呢,这就要考验国家的性质。大体而言,小国比大国、单一民族国家比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国家比分裂的国家、封闭的国家比开放的国家,更容易提炼共同性即国民性。可惜这四种情形,中国顶多占有一种半,而且细究起来,中国一直引以为豪的大一统,只具一种华丽的外形,这个泱泱大国,内部差异之大,简直势不两立,譬如一国之间,有南北之争,北方人视南方人为南蛮,南方人视北方人为北侉,北方人嘲笑南方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南方人嘲笑北方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省之间,像安徽省,皖北与皖南形同两个世界(有一说,则将安徽分三界),语言、饮食、风俗、习性等,无一共通,我曾开玩笑说,这一百年来,皖南人的杰出代表是胡适,皖北人的形象代表是释永信,这两个人身上有多少相似的国民性呢?甚至一市之间,不乏歧异,以浙江宁波为例,北三县人精细,南三县人则豪爽;听说有些县城,东边与西边,方言、人情,都不相同。
national character还可译作民族性,以此译名,愈发可见它与中国格格不入。不消说参差多态的五十六个民族,就拿“五族共和”的这五个民族来说,它们之间,有几多共同性可言?
质言之,国民性及其理论,在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的确成立,在中国,却显得大而无当、语焉不详。强行移植,必生谬种。那些关于中国人之国民性尤其是劣根性的论述,实则无关国民性,其主旨则是人性。试举最经典的一幕:鲁迅在日本学医,观看日俄战争(在中国作战)的画片,日本人公开处决为俄国做军事侦探的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然而,这样的看客心理,是中国所独有么,是中国人所一致拥有么,它的根源,究竟在于制度和文化,还是人性的幽暗意识?
如果可以明确,我们的国民性批判,其实是一种人性批判,则不难推论,所谓国民性改造,本质上则是在改造人性: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发源(如中州古籍出版《新民说》,副标题即“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由鲁迅“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即‘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为深化,至毛泽东“灵魂深处闹革命”而高潮,一脉相承,激荡百年。这其中,以“灵魂革命”对人性的改造最为显著,同时结局最为恶劣,不仅未能净化灵魂,反倒激发了人性最污秽、阴毒的一面,我们至今犹活在其阴影之下。
因为说到底,人性本不可改造。约瑟夫·康拉德曾对乔治·威尔斯说:“我们俩的思想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你并不关心人性,但认为人性应该得到改善。我热爱人性,但知道人性不会得到改善!”如果你站在康拉德这一边,显然不会赞同国民性理论与改造国民性的种种方案,反而会认为这是一条歧途。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开头,来说第二个细节。为什么那么多先贤热衷于谈论国民性呢?百年以来,论中国人之国民性的著作,不知凡几,除了鲁迅,还有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等,都是名著,一时风靡。我推测这背后的原因,不仅出于对西方理论的迷信,还出于对宏大概念、宏大叙事的迷信:言必称“中国人”,何其风光,何其堂皇;找出中国人的劣根性,然后加以改造,仿佛中国即可得救。这样的心理和思维,往好了说,叫焦灼,往坏了说,正体现了知识的僭妄。
于是我想起了两句话。一者出自胡适。1933年12月13日,胡适致信北大学生孙长元,说孙氏的文章有一个大毛病,喜欢使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此外如“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亦属此类。这便是所谓的“文字障”、“名词障”,皆为思想的绝大障碍。他在信末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
另一者,则是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结尾对读者的提醒:“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
2015年11月6日
钱理群:鲁迅为什么终生关注国民性?
鲁迅在1902年就和许寿裳先生讨论过什么是理性的人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病根,病根何在?这个问题是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思考的,鲁迅终生都在考虑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问题。
为什么他这么重视中国人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呢?因为这跟他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有关。1905年他就提出,中国要立国,关键是要“立人”。他所讲的“立人”主要指向个体的、精神自由的人。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近代文明(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现代文明)。他说,仅仅只有物质丰富,仅仅只有科技发达,甚至仅仅只有议会民主,那还不叫现代文明,关键是要“立人”,要个体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即使物质丰富了,科技发达了,有了议会民主,如果中国人没有个体的精神自由,那么中国还不能说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所以他把“立人”,把个体精神自由,作为他的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可以说,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现象的关注就成了鲁迅思想的核心。学术界有朋友认为,鲁迅思想是以改变人类精神为宗旨的精神哲学和精神诗学,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但是另一方面,鲁迅作为一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思想家,他并没有抽象地讨论人的精神问题,而是更具体地关注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精神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被鲁迅提出来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太多,我只讲其中的三点。
第一,中国国民性当中的奴性问题。鲁迅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他说的所谓中国的历史是一个“一治一乱”的历史。所谓“一治”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谓“一乱”就是想做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因此,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一个循环。
第二,鲁迅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近代史有一个判断。他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这是鲁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判断。在我看来,他的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
一个接近鲁迅的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说,鲁迅的生活、著作中用得最频繁的词就是奴隶,也就是说奴隶是直接触动他内心的一个现实,是缠绕他的一切思考的,而且鲁迅发现了中国人有三重奴隶状态:首先,中国人是中国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文化的奴隶。其次,中国人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文明的奴隶。他对这两种传统的和西方的文明失望以后,曾经寄希望于第三种文化。他认为第三种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呢?是一种使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文化,但他很快就在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现了新的奴隶,发现了革命工头,发现了奴隶总管。他发现,虽然目标好像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的现象,而实际的后果却是产生了新的奴隶关系。
因此在鲁迅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实际上不断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奴隶关系,是一个奴隶关系不断再生产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如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此,以后的社会也依然如此,始终有一个奴隶制度、奴隶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是非常沉重的,而且鲁迅还发现中国知识分子有不断被奴化的危险。对此,他提出有三大陷阱:第一,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官的“帮忙”和“帮闲”;第二,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商人、商业的“帮忙”和“帮闲”;第三,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大众的“帮忙”和“帮闲”。而在我看来,我们至今没有走出这三大陷阱来。
这样的一种不断再生产的奴隶关系就造成了中国人的奴化、中国人的奴性。鲁迅要揭露的是中国特有的奴性,所以我也只能概括地说一说。首先中国特有的奴性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的奴性实际上不是单独的奴性,它是跟主人性结合在一起的,叫“主奴互换”。什么意思呢?他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结构当中,对上是奴才,对下就是主人,所以他说,“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中国人有权的时候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这就是主奴互换。还有几个特色,简单地说:第一,不悟自己之为奴,就是明明自己是奴隶,但是不感觉;第二,容易变成奴隶,但是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第三,纵然是奴隶,还处之泰然;第四,当奴隶还要面子;第五,精神胜利法;……这都是中国特有的奴性。
第三,鲁迅对中国社会有两个非常严峻的判断:第一个判断,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食人”的民族,就是吃人的民族,中国到处摆着吃人的宴席。这里讲吃人(食人)有三个含义:一个是真的吃人,真的杀人,譬如在大饥荒的年代出现过人吃人的现象。还有一种是为革命而杀人,为革命而吃人。鲁迅有一个形象的概括,他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史。第三种就是精神的吃人,实际上就是鲁迅说的剥夺人的个体的精神自由。他说了一句非常沉重的话,说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因此就不把生命当回事了。我认为,这种对人的生命的漠视,恐怕是中国国民性的一个最基本的弱点。
鲁迅对中国还有一个很严酷的判断,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人“大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民众总是戏剧的看客”。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鲁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我觉得这话非常深刻,在这样一个语境下面,如果你真的相信别人说的话,那就是笨,那就是不合时宜。问题是谁都知道在说谎,谁都知道是假的,但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愿意做出相信谎言的样子。我们每天都在说谎,时时刻刻在欺骗,我也知道你骗我,但是我说对对对,相信你。这就是游戏规则。如果有人破坏游戏规则,说句真话,大家会觉得这个人不懂规矩,这个人太不成熟了,太幼稚了,然后大家一起把他灭掉。
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说谎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瞒和骗,不敢正视现实生活的问题,于是无不满、无不平、无思考、无反抗,于是天下太平。另一个就是不认真,一切都以游戏态度处之,最后变成哈哈一笑。而鲁迅说,中国恐怕就要亡在这个哈哈一笑上。这就是瞒和骗与不认真,是中国国民性的另外两个大弱点。
我们总结起来看,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第一是中国人的奴性;第二是中国人对生命的漠视;第三是中国人的瞒和骗;第四是中国人的不认真。这些都构成中国国民性的基本弱点,而且在我看来于今为烈。
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
但是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批判国民性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他不仅批判国民性,他更严肃地批判知识分子。在他看来,如果要启蒙的话,首先要启知识分子之蒙,这一点跟很多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大不一样。我还要补充的是,鲁迅不但批判国民性,不但批判知识分子,他更把自己放进去,更无情地批判自己。大家读过《狂人日记》,肯定还记得,他说几千年的吃人社会最后发现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尝没有吃过人,所以最后他都归于自己的一种反省,一种对自己的批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打掉自己灵魂深处的“鬼气”。我们批判国民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打鬼,但是在鲁迅看来,这个打鬼首先是打自己灵魂的鬼。在这点上,鲁迅跟胡适可能有点区别。胡适也是打鬼英雄,但他打的是别人的鬼,是国民性的鬼,而鲁迅打得更多的是自己灵魂的鬼。因此,对鲁迅来说,批判国民性——“打鬼”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讨论,更是灵魂的搏斗。
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
另外,鲁迅不仅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更发觉中国人灵魂中可贵的精神。鲁迅曾经写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中国人不只有自信力,还有他信力。问题是,中国人怎么才能有自信力,我们自信力应该建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眼睛里只看见中国那些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你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的。现在也这样,如果你只看到当官的,只看到某些知识分子,你会非常绝望。但是鲁迅说,我们的眼睛要看地底下,往下看,在地底下就有中国的脊梁。他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了呢?他们有自信、不自欺;他们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我以为鲁迅这里说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有自信、不自欺”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内在力量,尤其是我们今天要讨论重新建立国民真精神的一个精神的资源。
我还补充一点的是,鲁迅自己不仅继承了中国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而且在这个基础上他创造出了新的精神,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鲁迅精神。而在我看来,鲁迅精神是我们今天重建中国国民性,重新创造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的非常宝贵的资源。什么是鲁迅精神呢?我曾经概括三点:第一点,硬骨头精神;第二点,韧性精神;第三点,泥土精神。这三大精神我过去都讲过,今天时间来不及,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