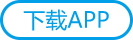当下青年是虚无的一代?
来源: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微信公众号
作者:杨庆祥、金理、黄平
杨庆祥:历史虚无主义的华丽上演
1980年代“潘晓们”提出问题被历史匆匆终结,也就意味着中国当代精神的深层构造其实并没有完成。在这样的历史传承中,80后的主体建构面临着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困境。在现实的层面上,大历史失效了,在精神的层面上,虚无主义滋生。这几乎是同构的过程。以我个人为例,1980年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之时,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吃饱饭没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我对饥饿是没有记忆的。1989年对于我们依然是空白,我对此唯一的记忆就是发现晚上有很多人围着一个收音机在听广播,然后间或听到大人们在议论什么,但基本上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丝毫没有影响到日常的生活。1992年我正在上初中二年级,市场经济的大幕虽然已经全面拉开,但是对于面临巨大升学压力的中学生而言,除了发现每个学期会有几个同学辍学之外(他们大多选择去南方打工),也没体验到这一历史对于我们产生的影响。然后是2003年的SARS事件,我们被圈在大学校园里面唱歌跳舞,除了不能出校门之外,我们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再后来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众多的80涌入汶川,争当志愿者,这成为一个“大事件”被媒体所广泛关注,并以此判定80后的责任意识的确立。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夸大其词的说法,在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我就立即打电话约朋友一起报名参加志愿者,需要反思的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并不是要去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志愿者”,而是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应该成为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或者说,我必须找到一种在历史之内的感觉和体验。我随后为自己的这一想法而惭愧万分,与数十万葬送的生命相比,站在历史现场的想法太过于自私自利。我知道一个80后诗人很冲动地就去了现场,但是因为完全没有志愿者的经验,他立即就感染上了细菌,然后成为了一个被“救治者”,更荒唐的是,他不停地打电话给很多人倾诉和求助,并抱怨当地的医疗和饮食。也许会有很多青年人的真实想法是为了尽一份力量,但是,也不能排除很多人是和我一样的想法,地震被视为一个历史的嘉年华,一幕无与伦比的大戏剧,我们希望参演成为戏剧的主体。我当然放弃了做志愿者的诉求,但这件事刺激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一场大灾难会变成一个大狂欢?也许这恰好证明了历史在我们身上的缺席。
对于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来说,上面我列举的种种历史事件已经证明这一段历史同样是充满了戏剧和动感的,但是与“十七年”和“文革”中的诸多历史事件比起来,这些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历史发生了,但是历史的发生并没有立即对个体的生活产生影响。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在80后的成长中,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只有在很少的时候,历史和生活才发生了对接的可能,比如大地震,正因为这种机会是如此之少,才有那么狂热的历史参与症状。从这个意义上说,80后是历史存在感缺席的一代。因为这种历史存在感的缺席,导致了80后面对历史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一就是如大地震以及奥运圣火传递仪式上体现出来的对历史参与的高度的热情,在这样一种参与中,80后找到了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存在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暂时性”表明了这种存在感的虚无;这就是第二点,因为对于历史存在已经失去了信任,索性就彻底放弃了这种历史的维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这是在80后青年人中更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倾向。
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在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中,他们日常言行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完全无视一个事情的性质和范畴,而用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和语气来对其进行嘲讽和戏谑。这种戏谑与90年代以来流行的王朔式的调侃完全不一样,在王朔那里,调侃的对象始终有一个指向,那就是僵硬的意识形态,但是,80后的这些调侃是完全任意性的,并没有什么目的,在这种言行中,生活本身的严肃性被取消了。今天的80后青年人非常善于模仿生活,但是,却不会自己构建一个真正有效的生活。你可以和他们成为朋友,但你没有办法与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交流。在历史虚无主义中,事物的神圣性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80后的主体呈现出了什么特征?
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时代的阅读症候里面窥探出什么。2010年在中国文学界比较热闹的事情之一就是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刊载了80后作家郭敬明的《爵迹》,由此引起了不同的意见和纷争,反对者以为这是文学向市场和庸俗阅读趣味的投诚;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文学观念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新变。抛开文学趣味和文学观念的差异不谈,毋庸置疑,郭敬明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神话之一。《小时代》在《人民文学》上刊登时,当期《人民文学》销售一空并不得不加印,这是90年代以来《人民文学》唯一一次加印。而《收获》同样因为刊发《爵迹》而销售量翻倍。批评家郜元宝在《评<爵迹>》的文章中遍挑语病,极尽嘲讽挖苦,这种批评虽然解恨,但在我看来却完全没有找到要害。虽然我同样鄙夷郭敬明小说中的技术含量,并对郭敬明如此“成功”满怀“嫉妒”,但我还是试图去理解这样一种写作和阅读。这里面肯定是内涵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以往的文学经验和阅读经验已经不可解释了。7月份我在安徽图书城买到了《小时代1.0》,我的预设是,我肯定看不下去这本书,因为它浅薄、庸俗和无知。但出乎我的意料是,我以极快的速度把这本书读完了。而与此同时阅读的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却被我一再搁置,最后不了了之。真实的阅读体验颠覆了预设的文学认知。我突然意识到,在我身处的时代,阅读和思考分离了。阅读仅仅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才有效,而思考可能与此相关,也可能与此毫无关联。阅读现在执行的是完全快乐的原则,它并不在意它能提供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程序,你按照这样一个程序来完成阅读,同时也就获得了快感。有一天下午我带着《小时代》去一家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书掉在地上,里面随书赠送的郭敬明的照片滑落出来,我的理发师帮我拾起来,问了一句话:“这是谁家理发店发的宣传册啊?”这句无心之语饶有趣味,他以一个完全局外人的身份来看郭敬明的时候,他认定其不过是一个“理发师”,其理由是郭敬明“精致”的妆容和“时尚”的发型。作家不再是忧心忡忡,蹙眉深思的“大作者”了,他现在是一个表象化的演员,写作被取消了“内面”。在《小时代》的扉页里有一张三十二开的彩色插图:一群俊男靓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聚集,其中一位男子坐在一个大镜子前,两个女性在旁边为他整理头发和衣服,另外几个男女在一角窃窃私语,还有一个女性站在另一边,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似乎在拍摄一切。我觉得这幅插图比任何郭敬明的小说都更能表明我们这个时代(郭敬明所谓的小时代)主体的存在状态。这里面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凸显的平面上,镜子和摄像机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看到(阅读)自己。或者说,“镜子”和“摄像机”已经成为了“主体”,写作者和阅读者都必须通过这样的主体把自己“物化”,并找到存在的实感。也许我们可以想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在鲁迅的“看”与“被看”中,始终还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非常清醒地持有其主体意识,并对世界作出价值上的臧否。但是对于80后而言,这一第三者消失了,或者说,第三者已经完全把自己转化为一个同一性的身份,“看”与“被看”之间的主客体关系被抹平,在此,80后的主体——写作的主体(同时也是叙事者)和阅读的主体(被叙述者)——是一种完全“去距离”的、单一性的指涉物。写作和阅读的快感来自于这种距离的如此亲近,现在,写作者编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镜子和摄像头里面的镜像一样不真实——并邀请读者一起来放纵。在这种共同的迷醉中,主体相互指涉,互为镜像。那个理性的、坚固的、笛卡尔式主体消失了,但那个沉溺的、观感的、后现代式的轻的主体却无处不在。
郭敬明几乎是无意识地呈现了这一点,他最大的贡献也许是命名了一个时代——“小时代”,很有意思的是郭敬明的这种分裂和矛盾,一方面,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电影中,郭敬明都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大时代”,(显然,郭敬明主要从财富增值的角度去定义大时代),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几乎毫无痛苦感地将这个大时代“迷你化”,变成了一个minitimes。而这个minitimes又像一个庞大的象征物压迫着生活在这个时空中的所有人。——电影《小时代1》的一个镜头就是:巨大的minitimes标志(和上海的外滩建筑物一样充满诱惑和压迫感)自天而降,在它的空隙中,一群年轻人手舞足蹈地向观众走来。他们化庞大为“迷你”,将历史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动物,他们对于历史的唯一直接的反应也许就像在动物园里的一句不无矫情的惊叹:好可爱啊……
历史的虚无主义对于80后来说并非意味着没有历史,实际上,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分析过的,和所有时代的人一样,历史总是存在的。80后也轻易就能找到自我历史发展的关节点,并与宏大的叙事关联起来。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在80后这里,历史之“重”被刻意“轻”化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沉重历史负担的国度而言,每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动,但是,也许只有在80后的这一代年轻人这里,我们才能看到历史虚无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矫饰、华丽地上演,如此地没有痛苦感。

金理:从“虚无”中再生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最近一次引发议论,是来自于我的好友杨庆祥君的长文《80后,怎么办?》。提出问题的契机之一,源于下面这个细节: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两位师长一块从京郊驱车回城,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在高速公路上盘旋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两位前辈突然唱起了《沙家浜》……“我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是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以自然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50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的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学潮等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相比较之下,“这三十年的历史同样充满了变化和震荡”,但“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的序言中,同样发现了当下青年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的挫折感”,朱特感慨:“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觉得举棋不定”,你在60年代随便拉上一个走上街头的青年人交谈,都会发现那个群体“最典型的色调就是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正世界”。这里有意味的是朱特本人的态度,这两个时代也许他都不满意。虚无主义可能有问题,但“强历史”的时代同样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
《80后,怎么办?》的举荐者之一是北岛先生,我记得当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们崛起文坛时,这些青年人遭受的批判之一就是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庆祥所开启的讨论方向,决非贴标签式的指认;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研讨,在什么样的情境中所谓虚无的一代会登场,他们“不相信”的是何种历史,他们拒绝的是何种历史认知的态度……再具体一些,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反讽者”登场,虚无主义重临,“回收自我”(庆祥的用语)的“地下室人”又被召回?是什么样的历史动能,让喊着《回答》的一代从历史和世界中摆脱出来。如果“对症下药”,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将今天“80后”的立场召唤、阐述为“重回历史”,那么:首先,我们如何看待此前的那代青年人“出走”、“摆脱”的姿态?是因为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选择了错误的姿态,以致我们今天要承担这笔历史性的“债务”?其次,我们今天要重回的“历史”,就是他们曾经试图告别的“历史”吗(是一个东西吗?)……除开以上这些可能有所分歧的、具体的讨论面向,《80后,怎么办?》最具价值的地方,我想是痛切的自省意识,归结到一点:我们这代人如何诚恳而有效地建立与历史的关联。
1922年的时候,茅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青年的疲倦》。和今天一样,当时的舆论也在指责青年的暮气沉沉,但是茅盾却很为青年人叫屈:“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各派思想的交流,都足以使青年感得精神上的苦闷。青年的感觉愈锐敏,情绪愈热烈,愿望愈高远,则苦闷愈甚。他们中间或者也有因为不堪苦闷,转而宁愿无知无识,不闻不见,对于社会上一切大问题暂时取了冷淡的态度,例如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但是他们何曾忘记了那些大问题,他们的冷淡是反动,不是疲倦,换句话说,不是更无余力去注意,乃是愤激过度,不愿注意。”(茅盾:《青年的疲倦》,《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八期,1922年8月10日)这里提到的“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也正是“虚无党”的代表。
承接茅盾的意思,青年人的冷淡、虚无,恰是“反动”,恰证明“锐敏的感觉”、“热烈的情绪”与“高远的愿望”,还未被彻底压服、绞杀。我近年追踪阅读“80后”作家郑小驴的创作,从他择取的小说题材来看,抗战、解放、土改、反右、文革……几乎构成一幅庞大的现代史画卷,而且有些作品(比如《没伞的孩子跑得快》)涉及到的是在当代中国依然作为话语禁忌的历史创伤记忆。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青年人的努力忽略掉呢。再比如同样年轻的作家飞氘,他的中篇《蝴蝶效应》以科幻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是多重意义上的:首先是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与典籍,小说三章分别以逍遥游、沧浪之水、九章算术命名;其次是现代中国的思索与抗争,尤其通过鲁迅这个意象表达出来;再次是当下的流行趣味,引入大量西方科幻大片,这些大片已不仅仅是“外部”资源(你看那么多“80后”抱着重温童年记忆的心态而涌进电影院看《变形金刚》,你就无法再去区分这是外来的制作还是我们自己的趣味投射)。飞氘的作品是在以上几者杂糅的意义上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近年来文坛热议的关键词,我特别反感以某种“寻根”的姿态去拼凑太多浪漫与抽象的符号。飞氘倒是很忠实于中国青年人当下的生命经验。《蝴蝶效应》杂糅了那么多中西、古今、雅俗的资源,错杂、交织、重叠甚至凌乱,乍看上去特别吻合今天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表象。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一直想到鲁迅,这不仅是因为《蝴蝶效应》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在《异次元杀阵》的题名下再写“无物之阵”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小说集的题词“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就来自鲁迅;而是出于一个强烈的感受:今天我们身上密集了那么多眼花缭乱的语义、信息、符码,但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这恰是鲁迅式的辩证法“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竹内好语)。
鲁迅说“虚无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创立出来的名目”(并因此成为俄国以及世界现代思想史上的专有名词),即指《父与子》中的巴札罗夫,这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鲁迅由此区分两种虚无主义: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通过“否定”来“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导出真正精神性的生命价值坚守与意义创造;而中国“做戏的虚无党”“善于变化,毫无特操”(鲁迅:《马上支日记》)。当面对“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的“无物之阵”时(鲁迅:《这样的战士》),“虚无”,恰恰可以在积极意义上,指向一种主动否定现有环境秩序、正面质疑美丽而空洞的教条的力量。
由今天的青年作家上溯到鲁迅,最后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忠实于这样的当下处境—— 一方面沉迷于一个丰富、充裕甚至过剩、泛滥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各种“好名称”、“好花样”的背后产生“虚无”的自觉,最后“无中生有”。对于今天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其实并无现成的资源可以捡拾,唯如鲁迅所言,必须“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然,“无中生有”,通达真正生命意义的自由创造,这是至难的事情,必须出以卓绝的洞识、付出艰险的精神承担。也许,一切才刚刚开始……
黄平:历史深处的虚无——从“改革”起源阶段的一些文学片段说起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虚无”之一种,笔者这一两年沉迷于故纸堆,在几十年前的字缝深处,总觉得隐藏着“今天”的故事。现在关于“80后”在当下这个社会应该“怎么办”,似乎讨论的很热烈。这场讨论背后还是“青年的出路”这个老问题,当代中国的历史不过六十多年,这个问题已经几番沉浮,背后牵扯出多少于无声处的大戏,念之令人慨叹。具体到杨庆祥的长文《80后,怎么办?》,笔者写过《反讽者说》一类小文章予以唱和也予以商榷。这一次不再重复,还是回到历史,谈一些故纸堆中的零散片段。这也谈不上“以史为鉴”,因为我们其实还在那段“历史”之中。
在蒋子龙发表于1977年的《乔厂长上任记》中,有一个青年工人叫杜兵,这是乔厂长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工人,关于这两个人的相遇,小说是这么写的:
乔光朴在一个青年工人的机床前停住了。那小伙子干活不管不顾,把加工好的叶片随便往地上一丢,嘴里还哼着一支流行的外国歌曲。乔光朴拾起他加工好的零件检查着,大部分都有磕碰。他盯住小伙子,压住火气说: “别唱了。”
工人不认识他,流气地朝童贞挤挤眼,声音更大了:“哎呀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没出息。”
改革者乔厂长整顿山河,在小说中既要挑战官僚主义者冀申,又要说服杜兵这样的青年。杜兵这样的青年和冀申这样的官僚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提不起半点兴趣了。冀申们不信,但总要做出一副相信的样子,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在这套官话下进行着利益交换的勾当。冀申们的行径,杜兵们其实是看在眼里的,这更加剧了这些青年的虚无。
这种虚无如果要在当代史中找一个标志性的起源,起源于“林彪事件”。1970年代是灰色的,开场时分就是“副帅”的覆灭。深夜时分的蒙古草原上这一声巨响,“无产阶级革命家”旋即变成“资产阶级野心家”,“文革”的修辞怎样铿锵,到此都难免要顿一顿。强敌环伺,私心难灭,官僚制几番还魂,浩浩荡荡的一番革命理想,最终沦为广播中的高音与社论上的空谈。和激烈紧张的60年代相比,70年代变得松弛疲沓,尽管理论小组都开进了杜兵们的车间,“资产阶级法权”讨论的好不热烈,但盯着车床上空的马克思,杜兵们的眼神渐渐散了。
“改革”的起源阶段,怎么说服杜兵这样虚无的青年?乔厂长回厂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杜兵,这安排有深意存焉。有意味的是,乔厂长不讲半句“大道理”,而是就机床闸把的用法和杜兵展开具体的辩论。小说下一段安排怒气冲冲的乔厂长走进隔壁的七车间,迎面一台从德国进口的二百六镗床,西门子公司派来的德国小青年台尔忙上忙下。这个小青年不是什么正面典型,从德国来中国的中途偷偷跑到日本游山玩水,到厂子报到的时候晚了一周。台尔自知理亏,卖力工作,以高超的技术不到三天时间就把十天的工作都做完了。蒋子龙叙述到此特谓点题:“他的特点就是专、精。下班会玩,玩起来胆子大得很;上班会干,真能干;工作态度也很好。”
“下班/上班”、“玩/干”的分离,表明乔厂长尽管是从五十年代来到七十年代的尾声,但已经不准备重复当年的老办法——依赖政治动员与思想工作将“业余生活”转化为劳动时间。天翻地覆慨而慷,七十年代末的车间,乔厂长已经自觉地向工人的“私生活”让步,困扰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公”与“私”的辩论在此偃旗息鼓。乔厂长所关切的是,怎么让杜兵们在工作时间尊重职业伦理,提高生产效率,变成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业”人才。
新时期这种“红”与“专”的转化,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中被第一次道破。不了解七十年代的读者,会以为《哥德巴赫猜想》的主人公陈景润在“文革”期间饱受委屈,殊不知陈景润是第四届人大代表,享受颇高的政治待遇。在“五一”劳动节游园欢庆、“十一”国庆节招待宴请中,陈景润作为“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界人士代表”都有出席。好出惊人语的江青,更是批示过“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这在各种公开出版的陈景润传记中都有清楚地记载。
如果不了解“文革政治”征用陈景润的这段“前史”,那么很难理解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历史内涵。从“文革政治”到“改革政治”,不仅仅在于是否重视“知识”,也在于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在“文革政治”的框架中,对于“知识”并非全然不重视,但始终强调“政治挂帅”,以“政治方向”统领具体的专业探索。江青及其背后的“文革政治”是从“独立自主”这个角度来阐释陈景润的数学成就。但是在新时期开始之后,这套逻辑被予以颠覆,“知识”与“政治”开始分离,开始变得纯粹化与专业化,对应于去政治的、专业化的“新人”。一言以概况的话,二者的核心差异,落实在“红”与“专”的辩证。
《哥德巴赫猜想》潜在的对话对象,正是50-70年代“又红又专”这套论述。徐迟扭转了陈景润“白专”的形象,将“红”从“政治方向”转化到“为生产服务”,“红”本身变得技术化了,“红”与“专”的等级次序发生了微妙的颠倒。《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对于“新时期”极为重要,在于通过塑造陈景润这个典型,将“政治的人”转化为“专业的人”。
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其意义不仅针对知识分子与科学研究,更是将“文革政治”的“政治的人”,转化为“改革政治”的“专业的人”,扭转了我们对于“人性”的想象,为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建设”以及背后的科层制社会,生产出对应的感觉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陈景润成为了“新时期”的“典型”。
正是在“专业”这一点上,乔厂长对于德国青年大为赞叹,并以此作为杜兵们的榜样。陈景润的“专业”依赖于怪癖一般的数学天赋,难以普遍推广,真正可以普遍化的做法,是利用“竞争”机制,将原来的共同体打散,将“集体”转化为竞争关系中的“个体”。这正是乔厂长治厂的第一招,小说这样写道:
他首先把九千多名职工一下子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通过考核评议,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在业务上稀松二五眼的,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汗的,占着茅坑不屙屎的,溜奸滑蹭的,全成了编余人员。留下的都一个萝卜顶一个坑,兵是精兵,将是强将。这样,整顿一个车间就上来一个车间,电机厂劳动生产率立刻提高了一大截。群众中那种懒洋洋、好坏不分的松松垮垮劲儿,一下子变成了有对比、有竞争的热烈紧张气氛。
与之相匹配,乔厂长以“物质刺激”维系这套竞争机制,对于优胜者许诺以丰厚的物质回报,这是乔厂长治厂的第二招:
他说全面完成任务就实行物质奖励,八月份电机厂工人第一次接到了奖金。黄玉辉小组提前十天完成任务,他写去一封表扬信,里面附了一百五十元钱。凡是那些技术上有一套,生产上肯卖劲,总之是正儿八经的工人,都说乔光朴是再好没有的厂长了。
不要小看乔厂长的这两招,回望过去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人性上的核心驱动就集于此。杜兵似乎也不再幻灭了,在《乔厂长后传》里,杜兵从政治漫画的能手转变为产品设计的专家,“美术”被转化为“技术”,这种技术化的大转身,对于后来的“文学”与“政治”也莫不如此。乔厂长似乎相信,只要找到杜兵们的专业岗位,并且给予有效刺激的物质回报,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乔厂长上任记》姊妹篇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里,蒋子龙更是不惜将团支部书记解净推到“落后青年”刘思佳的怀抱,刘思佳也不负厚望,设计出一套工厂的技术化管理。在小说里党委书记祝同康不再是指引道路的巨人了;相反,却是一个有着“像婴儿的头发”的虚弱的老人,内心犹疑、惶惑,“越来越感到难以适应自己的工作了”。当他面对解净的时候,心头感到压抑,“反而不敢看她了”。他省悟到:“他在她的眼里不再是党的化身,也不是父亲式的人物了。”
“专业技术—物质刺激”这套逻辑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然而作为官僚主义化身的冀申们隐匿在文本的深处,冷眼看着乔厂长的折腾与杜兵们的奋起。在未来,冀申将像一个恶性肿瘤一样不断在乔厂长这套机制内部膨胀,以他密密麻麻的关系网堵塞住杜兵们的上升空间。当未来的杜兵有一天发现,尽管他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优等生,在单位里也是专业能手素质出色,却无论怎么努力也换不回感到满足的物质回报,他恐怕会慢慢地考虑“思想”问题。在那一刻,他恐怕要再一次地穿越“虚无”。
(原刊《长江文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