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的小说与我们的焦虑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张柠
1、紧身衣和脑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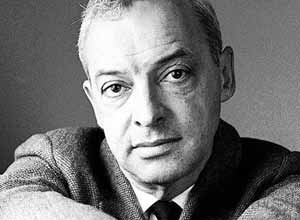
第一次读到索尔·贝娄的小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还在大学校园里。那时候,大家都一个劲儿在读博尔赫斯、罗布格里耶、卡尔维诺,还有戴维洛奇和昆德拉。批评界也在开始大谈所谓“后现代”了。大家似乎对索尔·贝娄的现实主义写法兴趣不大,而是着迷小说叙事的形式创新。实际上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正在接近索尔·贝娄开始文学创作的时代状况。物质主义的病毒,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护航下已经在身边悄悄弥漫,对精神生活的原有程序在进行彻底的改写,传统浪漫主义的“英雄”戏剧已经开始谢幕了,日常生活的“小丑原型”正在粉墨登场。但在众多的“小丑原型”的包围中,还有少数从由原来的“英雄原型”蜕化变质而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当时我被索尔·贝娄风趣、幽默、机智的叙事,还有略带刻毒的人物刻画手法吸引住了,也被他笔下那些有“精神分裂症”的知识分子(比如赫索格、洪堡、西特林等)形象吸引住了。尽管我们在学术讨论中大谈“现代派”、“后现代派”(无论对外部世界还是内部世界而言,这都是十分安全的);实际上索尔·贝娄布下的那个阴影一直深埋在我们心底。我们的确有一点拿赫索格自况的味道,朋友之间互相经常用一句话来相互取笑:“你再罗嗦,就给你穿上紧身衣!”
穿紧身衣(一种布料中有橡皮筋儿的特制服装),是精神病院的一种常规的辅助治疗方法,目的在于抑制精神病人的亢奋。从社会角度看,这种亢奋症状实际上就是传统浪漫主义的第二代进化形态(第一代进化形态是肺结核,托马斯·曼和屠格涅夫对此有详细描写)。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就经常接受这种穿紧身衣的治疗。赫索格是精神病人吗?我至今还没弄明白;医生也没有完全确诊,只是在他情绪过于反常、举止过于怪诞的时候才给他穿紧身衣。至于他的精神是否正常,连赫索格自己也拿不准。他自己说:“我要是真的疯了,也没什么,我不在乎。”假如赫索格精神正常的话,那么究竟是谁生病了呢?毫无疑问,那就是他周围的人有病。关于这一点,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真正权威的标准。法国思想家福科曾经为此绞尽脑汁,还著书立说,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少数人被迫穿紧身衣,多数需要穿紧身衣的人“逍遥法外”的局面。
后现代理论家已经签署了“人物”的死亡通知书(没有“人”,只有“物”)。但几十年过去了,那些人还没死,他们只不过是在充满病毒的环境里“生病了”。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只是被紧身衣束缚着不能动弹。尽管他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已经被分解,但他们的大脑还在急速运转。当代医学关于“脑死亡”(Brain Death)的规定,好像是在为这些人的存在权力提供了一线生机,并对貌似繁荣的虚假生活(索尔·贝娄称之为“活着的死”)进行宣判。
2、没有地址的书信
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写的是一位孤独的军官,天天盼望别人给他写信,自己却从不给别人写信(其实他一封信也没收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英雄”后遗症。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的主人公、“懦弱”的赫索格恰恰相反,从来没有人给他写信,而他一生都在不断地给别人(前妻、情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国家议员、尼采、布莱尔、同事、纽约时报的编辑)写信,但一封信也没有发出去,全部装在他的旅行手提包里。他在想象中将信一一发出去了,于是一边旅行,一边继续不断地写,写着一封封没有地址的书信。
赫索格一生最喜欢的两件事:旅行和写信。其实这不过是一件事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旅行是抵达也是逃亡。写信是交流也是回避。此前的长篇小说《雨王汉德森》中,索尔·贝娄就讲述了一个因拒绝现代生活而逃亡非洲故事。但他假设了一个带着理想返回的结局(类似于大团圆结局)。在《赫索格》中,这种旅行成了漫无目标、永无尽头的流浪。就像他那一封封在现实中没有收件人的书信一样。这是一种让人感到非常绝望的旅途。
《纽约时报书评》在《赫索格》出版的那一年(1964),发表了一篇题为《连锁信》的书评,说赫索格那些疯疯癫癫的书信断片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了一个时代的信条:这个时代是一个可怕的深渊……神志正常的旧定义对这趟旅程并没有帮助……但爱、公义、知性和感性依然重要,而不是与暴力和威胁泰然共处。
赫索格正是一个为寻求爱和公义而渴望交流的人,但他无法找到、或者不敢面对交流的对象,他被他的时代所拒绝,或者说他拒绝了他的时代。于是,他在想象中将所有人都当成交流的对象,渴望跟他们亲切交谈,诉说衷肠;但他采取了一种既能够交流,又不在场的形式——写信,而且一封也不寄出去。他独自一人在想象中与收件人一起分享着精神的乐趣。
索尔·贝娄写作《赫索格》的时候还没有网络和手机,人们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进行交流。手写的书信,今天的人已经很陌生了。人们相互交流的信息已经变成了电子信息在太空中飞舞,群发到所有人的手中,这是另一种“没有收信人”的形式。我们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在烛光中写下对一个人的思念,然后用口水将邮票沾上,独自一人在雨夜穿过林荫道,用颤抖的手将信投进邮筒。
3、晃来晃去的女人
小说主人公与异性的关系,无疑也是一块人生和社会的试金石。索尔·贝娄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写了主人公约瑟夫对人生(自由)的厌倦,对婚姻和家庭的绝望,他宁愿重新回到“不自由”的军队去。到了《赫索格》中,这种奇怪的英雄主义情结,已经变成另一种形式。他默默承受着一种自身的懦夫状态,在妻子、情人和日常生活面前。这种懦弱状态,是传统的精神价值和现实的物质主义双重逼迫的产物,因此这既不是左派,也不是自由派,只能是懦弱派。
赫索格是少有的正人君子。或许这正是他的缺陷,他第一个妻子因此抛弃了他,为了探望子女,他只好经常忍受前妻的奚落。第二个妻子马德琳跟一位他们俩的共同朋友跑了。无家可归是赫索格旅行和不断写信的前提。他仿佛一条千里寻家的狗在中途奔波。他反对老师跟学生发生男女关系,维护师道尊严。正是这一点,被他任课的夜校的学生雷蒙娜相中了。雷蒙娜认为,到处都是坏蛋,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已经很少见了,于是主她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当然,赫索格不是没有弱点的。比如,他非常欣赏女性的乳房,认为这是艺术品。雷蒙娜正好发现了他的这个“死穴”。
在赫索格眼中,所有的女性婚前都是他所憧憬的艺术的化身,婚后都成了他的生活导师,指导他如何介入现实生活。女性变幻莫测的性格令赫索格头晕目眩。经过两次离婚之后,赫索格已经丧失了爱的勇气。面对雷蒙娜,他简直是在东躲西藏,这是他的认真之处。第三个女人雷蒙娜,注定只能伴随着他的漫无目标的旅行和不断书写却不寄出的书信一起,在“爱”的中途游荡。
尽管在小说结尾的时候,雷蒙娜依然在他身边,但赫索格已经丧失了交流的热情,“他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信息。没有,一个字也没有。”这是一种交流愿望的最终的和绝望的消亡,一种必然的失败。最后的交流渠道毁灭了。社会价值的崩溃是从最小单元(家庭)开始的,也是从最隐秘的个人情感领域开始的。欺骗、犯罪、吸毒、淫乱等一系列人类的邪恶品质,也都是因为最后的底线(家庭)崩溃而导致的。
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索尔·贝娄夸大了文学和美学的作用。他将希望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其思想有保守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他跟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是同道)。他说除了现实,还有一种被忽略的真正现实。如果没有艺术,我们就看不见这种真正的现实。艺术能够找出日常生活背后的真正现实的本质来。我觉得他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味道。




